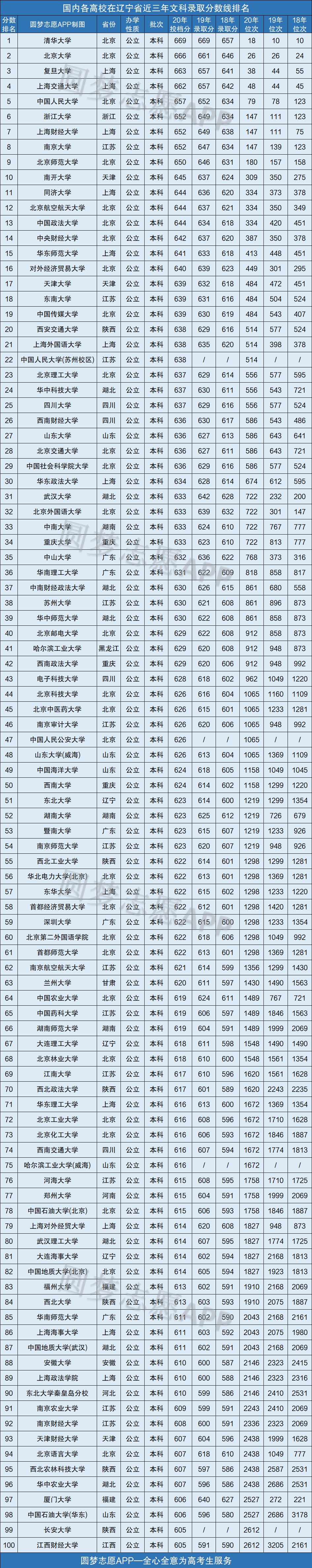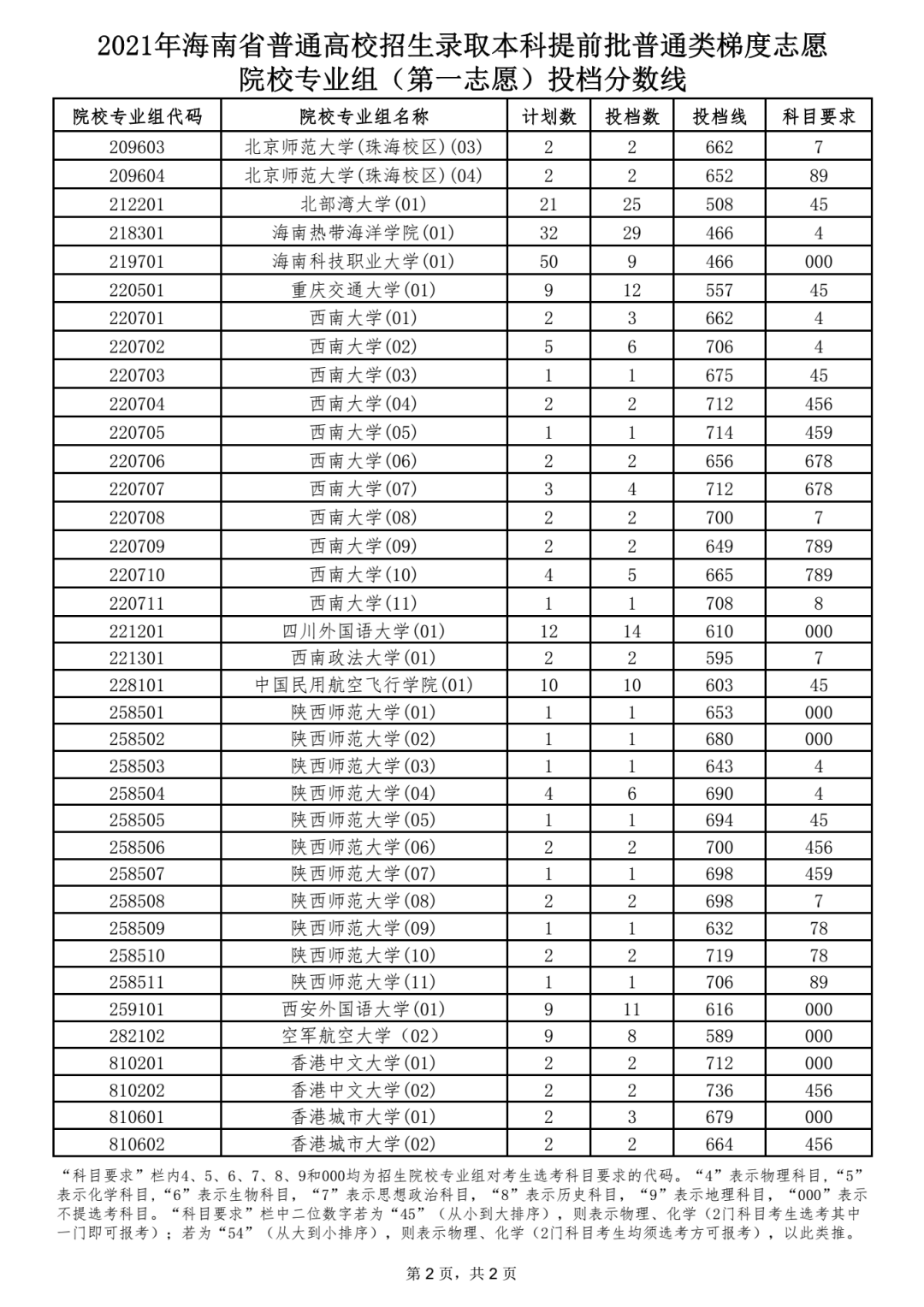编者注
2022 年 10 月 22 日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(原上海医科大学)
将庆祝其成立 95 周年。
九十五年风雨无阻,医学之路为人民不断前行。 一代又一代医者不改初心,始终以“服务人民、争强国”的精神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同行。 如今,上海医科大学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。 我们要时刻牢记前人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,汲取前人前进的智慧和力量。 复旦大学档案馆先后推出了《情尚医》系列文章,让我们聆听校友记忆中老医者的故事,感受大师的魅力,领会正医明道的精神。
在我心里,医疗是非常神圣的。 它是第一所由华人独立创办的国立高等医学院,创始人是高级院长严福清。 上海医科大学办学氛围严谨,师资力量雄厚。 20世纪50年代,考入全国一流的医学院——上海医科大学,是我一生的骄傲。
1950年上海医学院录取名单
戴仲英学习成绩表
对医学老师的第一印象
1950年我进入医学界时,院长是药理学专家朱恒弼,学术院长是生理学教授徐凤岩。 大学一年级,我们学习政治、数学、生物、化学、物理等基础课。 第二学期开始重点课程,包括解剖学、组织胚胎、定性和定量化学分析等。
20世纪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校门
在这些课程的老师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又奇老师。 王又奇老师是著名神经解剖学家Russmason的学生。 他说的是地道的南京话。 当他带我们去练习解剖时,他的太阳穴已经灰白了。 我们最钦佩他的是他对人体神经支配的熟悉。 当你找不到勇气的时候,就邀请他过来吧。 过了一会儿,神经就会用手术刀和镊子清晰地显示在你的眼前。 当我们刚进入医学界时,我们对医生的概念还比较模糊,更不用说涉及医德的问题了。 可以说,第一堂医生道德观念教育课是王友奇老师给我们上的。 那是一次解剖实习时,一名同学不自觉地用手术刀反复戳一具尸体的头部。 王老师见状,立即制止了他。 他郑重地对同学说:“这些尸体来之不易,为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,不允许有任何对尸体不尊重的行为!” 我还记得王友奇老师当时说的话。 非常清楚。
王又奇教授(左一)指导学生进行组织胚胎实验
第二年下学期,与临床实践直接相关的课程较多。 病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,由顾景谦教授教授。 顾老师很朴素,瘦瘦的,穿着一件洗白的蓝色布袄。 他看起来像个工人。 我记得我和同学于金去病理科找顾教授。 一位老人向我们走来。 于瑾以为他是工人,问道:“顾靖谦教授呢?” 老者一时愣住了。 犹豫了一下,他用地道的绍兴话回答:“我是顾靖谦。” 当时,于瑾尴尬极了。 他没想到,这么有名的教授,却穿着很普通的衣服。 病理课一开始,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病理学的重要性。 直到进入临床,我们才逐渐认识到,病理学不仅是任何医学分支的诊断依据,也是诊断某些疾病的金标准。
有趣的医学课
三年级下学期,我们进入了临床课程的学习阶段。 学科门类较多,包括内科、病理诊断、动物外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公共卫生等。 老师们都是一流的,授课简洁,引人入胜。
20世纪50年代东一号楼及中山医院全景
我还记得林兆奇教授在病理诊断课上讲杵状指时的场景。 那一次,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药杵给众人看,并问众人:“这是什么?” 学生们一时愣住了。 林教授等大家发言了一会儿,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字:药杵。 又说道:“杵是用来舂米或者洗衣服的,上端细,下端粗。这是药用杵,也是上端细,下端粗。今天我们要谈谈棒状手指。” 他还描述了一位患有慢性肺病的患者。 他举起手来,说道:“这是一根棒状的手指,远端粗,近端细。” 然后他解释了杵状指的原因和诊断意义。 就这样,泡吧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,永远不会再被遗忘。
林兆奇教授查房
公共卫生系苏德龙教授喜欢用一些有趣的问题来活跃课堂气氛,启发学生思考。 记得有一次讲到流行病学的预防,苏德龙教授问道:“现在一支大军要经过我国西南边境的一个疫区,有什么方法可以既预防疟疾感染又不影响行军速度呢?” ?”教室顿时热闹起来,同学们纷纷提出建议,有的说先准备大量的奎宁药片,有的则建议可以准备大量的蚊帐。突然,一位女同学提议道: “疟蚊的生活习性是晚上活动,白天休息。 部队行军时间可改为夜间行军,白天休息。 夜间行军时,人们不停地走动,蚊子很难叮人。”苏教授说,这种方法是最好的,因为它是根据蚊子的生活习性设计的,既省钱又有效。
苏德龙教授(中)与学生交流
严谨求实的医疗实践
上海的医生对病例的诊断非常严格。 我在神经内科接受了非常深刻的教育。 那次是张元昌教授查房。 当时,张元昌教授已经是国内非常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。 有一次,我收治了一位患有贫血和头痛的 13 或 14 岁患者。 门诊主治医生写的入院诊断书是“慢性砷中毒”。 我以为我已经仔细地进行了病史询问和体检,为张老师查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 但听完我的报告后,张老师问道:“你诊断他慢性砷中毒的依据是什么?” 我说:“他吃了很多含砷的补血药。” 张医生又问:“他多久了?服了多少剂量?砒霜的中毒剂量是多少?” 我无法回答。 张医生向家人要了一个药瓶,看了之后对我说:“这个涉及到毒理学,你需要知道你吃了多久的药、吃了多少药,才能确定是否中毒。我查过药理书,这个剂量不会引起砷中毒。” 他仔细地为年轻患者进行了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。 最后,他站着沉思了一会儿,对我们实习同学说:“我看这孩子还小,脑桥脚肿瘤预后不好。” 在那个没有CT、MRI的时代,张教授能够准确定位患者的脑部病变。 这样的技术确实令人惊叹。 这件事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。 收集病史是一门科学。 每个医生都要用自己的脑子,不能听别人说的。

在妇产医院实习期间,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王淑珍院长。 有一次,我们遇到一例子宫脱垂的病例。 患者需要接受阴道全子宫切除术和阴道前后壁修复术。 王淑珍院长主刀,我是助理。 手术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,中午结束。 王医生的手术细致务实,从不以速度卖弄技术。 她边做边解释。 解剖非常清晰,出血彻底,伤口缝合也非常顺利,所以出血很少。 手术后,患者体温未超过37.3℃。 王医生手术的患者术后很少出现发热,恢复很快,几天就可以出院。
王淑珍教授授课
当我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时,上海医科大学建校才20年左右。 上海医科大学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顶尖医学院? 由于上海医科大学老校长严福清目光远大,胸怀宽广,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,吸引了众多名师到上海医科大学任教。 20世纪50年代,上海医科大学共有教授80余人,其中一级教授16人。 他们朴实平易近人,医德高尚,同情贫苦百姓,严格执行上海医学院不贪污、不经商、不徇私的校规。 三个原则。 而且医风严谨,老师教学一丝不苟,对学生严格。 同时,上海医科大学的学术讨论非常自由。 大家各抒己见,各种意见和想法相互碰撞,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。 因此,只有有能力的校长、院长,众多的名师,严谨的学风,民主的学风,医学院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著名的医学院。 你说,我们这些学医的人为什么不为母校感到骄傲呢?
医学系1955届毕业生合影
本文作者戴中英,是上海医科大学1950级校友。
复旦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