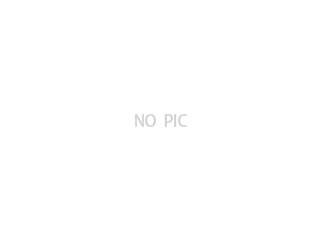我的老爸
一提起老爸我就头疼,别看他在外人面前像个面冬瓜似得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,可他的话都给我留着呐。他只要一见到我,那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上下嘴皮就吧嗒吧嗒个没完没了——我想他真应该去当演讲家——害的我每天都要聆听他的谆谆教诲警世通言。老爸的教学水平实在不敢恭维,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:要好好学习啦,不要贪玩啦,应该像个女孩子样啦……有时我听烦了,就会捂着耳朵大声抗议:“知道了!知道了!知道了!少说两句行不行?没人把你当哑巴。”每次他听了我的抗议,不但不生气,反而讲得更起劲了,真拿他没辙。
上学期期末考试,由于考试时粗心大意,数学考砸了。领成绩单那天,我心情沉重的离开了学校,学校离家不远,平日里五分钟就到家了,那天我却走了十几分钟,感觉就像过了一个世纪。我怕老爸,怕他那张不依不饶的嘴,怕他给我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课。
回到家,刚进门,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:“静静,这次考得咋样?”言语里透着关切和期冀。“不咋样……”我低着头,怯生生的回答。“我天天跟你讲,平时要多看书,多做题目,‘磨刀不误砍材功’,累不死你,可是你呢……”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懊悔,我不敢看他的脸,我知道他此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失望,我又何曾没用功呢,每天不都做到十一二点钟吗?我低着头,默默地流着泪,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讲些什么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老爸说得口干舌燥,终于不讲了。我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,老爸竟然足足讲了一个钟头。哎,命苦呀!
中午当我端起碗筷准备盛饭时,发现老爸似乎又要说些什么,忙说:“爸,《午间新闻》到了——新闻节目是老爸的最爱。”老爸一听,三步并作两步,飞快地走到电视机跟前,打开电视,关心他的国际国内大事去了。好险呀,又逃过一劫。
吃过午饭,我便打着“学习”的幌子,到同学家玩去了。然而,晚上一回到家,老爸就又给我上起了政治课。憋了半天的话的确厉害,那一串串语言,如同一架机关枪不停的“扫射”,害得我左右耳得了“神经性耳聋”。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,我便冲进卧室,“咣”的一声把门关上,躺在床上,戴上耳机,听起阿杜的新碟来,任凭老爸在门外暴跳如雷也好,伤心欲绝也罢,就是不开门。
第二天一大早,老爸还没有起床,我就背起书包去了补习班。当初老爸给我报名时,我是很不情愿的,但为了避免“耳膜炎”再次发作,两难相较择其轻,也只有硬着头皮去了。一出门,我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,“翻身得解放了”——这一下老爸就没有机会给我上政治课了,这样的时光真爽!
俗话说”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”,中午回家时,一上午愉快的心情又让老爸给破坏了,刚进门,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,就听老爸问道:“今天学什么,学得咋样,都听懂了吗?吃一堑要长一智,学习不是一日功夫,要日积月累,做到日日清月月清,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……”MY GOD!政治课又开始了。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如此,老爸也真够辛苦的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看着老爸眼角眉梢一天天增多的皱纹,我暗暗发誓,今后一定好好学习,争取优异的成绩,让老爸劳累了多年的上下嘴皮歇一歇,因为我爱我的“政治”老爸。
我有一个好父亲
父亲是一个少言的人。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,都是听见母亲一个人在不停的讲话,父亲只是一个劲的抽烟,偶尔才应答一下,那话也多半只是一两个字。家里来客人,父亲陪人家吃饭,既不让酒,也不劝饭。只自顾自吃自己的,显得很不礼貌的样子。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一样。他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,他觉得学习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有问题问他,他也是说你们还是去问老师吧。
父亲是个农民,但在我眼里很多地方又不像地道的农民。父亲读完了小学,初中上到了二年级就因贫困辍学了。接着他和几个同伴瞒着爷爷奶奶一口气跑到了包头,在那儿上了两年的中专。后来因为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学校解散了,父亲又回到家继续当他的农民。父亲写一笔很好的毛笔字,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,父亲总要被人家恭敬地请去当帐房先生,记记份子什么的。到了春节,更是父亲忙碌的时节,乡亲们都早早的把大红纸送到我家,请父亲写春联。往往春节未到,我家早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了。我小的时候习字,父亲就让我学着给山东的舅舅写信。什么格式,怎么称呼,如何落款,都是父亲手把手教我的。我虽然喜欢他的字,但我练字没长性,直到如今也没形没体儿的。回家陪父亲喝酒,喝到高兴处,父亲总是指着我说:“就你还中文系,还老师,写字还不如我这个农民哪。”我只能笑着点头。
父亲是个爱书的人。他每次出门,包里总要塞本书。实在没有可看的,也要捎上几张报纸。记得父亲亲手买的书有1975年出版的三卷本的〈水浒传〉、上下册的《东周列国故事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和冯梦龙的“三言”。农闲时节,别人家的男人或打牌或赌钱,我父亲就在炕上看书。逢雨雪天,更是整天抱着书看。这两年父亲眼花了,自己买个花镜,还是不忘读书。我有时端详端详,老人还真像个文人先生呢。今年暑假回家,我倒腾书柜,找出一套明朝抱翁老人的《今古奇观》来,是清朝道光年间刻印的,可惜少了一卷。我对他说,这书给我吧。父亲说行啊,反正我眼花也看不了了。父亲还常常感慨地对我说:“文革那会儿,你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留下来的书都让我作饭时当柴火给烧了,怕惹祸。要不留到现在也值钱了。”于是我也很感慨。好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再赶上“焚书”的年代了。
我家的三个孩子中,父亲最疼我,他说我坐得住,安分。冬天的时候,我整天在大街上疯跑,出了满身的汗,热得把穿的棉裤都溻湿了。早晨起床前,父亲总是早早把火炉点好,然后把我的棉裤用手翻转过来,一点一点地靠近炉子烤,边烤边慢慢晃动着,不一会儿,我就看见棉裤上腾起缕缕热气。等烤完了,父亲还要用他的两双大手把棉裤搓搓,让它柔软。等我再穿上的时候,感到很温暖。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他常常给我擦皮鞋,每次都收拾得很仔细。我上学骑的自行车,每天都是父亲为我取出来,晚上回到家,每次也是父亲为我存放好。擦车打气更是他的份内之事。在他眼里,我似乎永远是个孩子。我上学时读的书,都是父亲亲自包书皮,并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。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了,我上高中时的课本仍然保存完好。有时我读他说,这书都没用了,您把他卖了吧。父亲总是说:“放着吧,放着吧,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”我在南京上四年大学,每次都是父亲执笔给我写信,信的结尾总是说,别心疼钱,吃好,注意身体。他很少叮嘱我好好读书,但我读了父亲的信,自然知道该怎样去念书的。
现在,我当父亲也十多年了。孩子小的时候,因为他生病不肯吃药,没少暴打孩子,大一点了,因为不爱去幼儿园又挨了我不少打。直到现在,学习不好了,考试不好了,我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。想想父亲对我,再想想我对孩子,确实很惭愧啊。我和父亲每年相见几次,见一次,他就老一点儿。可不是吗,我都奔四十了,父亲能不老吗。
在我眼里,父亲是个沉默的人,是个爱我疼我的人,是个爱读书写字的人,是个引导多于管束的人。在我眼里,父亲的形象很高大,须仰视才见。愿父亲能健康的活着,我愿意永远做他的孩子。
一篇写人作文 要精华700字
300字作文2021-04-15 09:54:41网络
上一篇:
求写人的作文.字数400至500
下一篇:
写事作文400字左右